Escaping the golden cage
生活在国外的瑞士人逃离金丝笼
尼古拉斯·穆勒
商业计划在一个迎头赶上的国家里取得领先文:Susan Misicka,图:Daniele Mattioli
尼古拉斯·穆勒 上海MBA学生
尼古拉斯·穆勒 上海MBA学生


对尼古拉斯·穆勒(Niklaus Mueller)来说,中国是必处之地;五年之内,他已第三次去中国生活。像他这一代的很多瑞士人一样,这位32岁的年轻人渴望探索世界,并为未来积攒经验。。
不那么典型的,却是他正在逆流而上。“我有很多朋友想往西走,我却想回到东方。中国令我着迷,尽管我已在那里度过两年多时光,我觉得还能加深自己对她和她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的了解,”穆勒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
衣着整洁的穆勒带着自己的笔记来接受采访,看起来他是个考虑周到、有备而来的人。穆勒与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2011年,他得到CMS国际法公司在中国的实习机会。虽然他得在2012年回苏黎世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但中国留在了他的脑海中。
“我已经确信,自己必须想办法回中国,”穆勒回忆道。CMS公司给了他机会回到上海,以全职合伙人的身份开始自己的事业,他在那里工作了两年。
然而总不能在自己实习过的地方呆一辈子啊,因此穆勒换了工作,加盟苏黎世的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在那里工作一年后,中国仍在召唤他-于是2015年他注册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我对创业精神与创新能力非常感兴趣,鉴于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我认为她是最令人激动、值得一去的地方之一,”来自伯尔尼的穆勒解释道。
这种激动之情还延伸到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以及语言的热爱。“每个字背后似乎都有一个故事,努力了解这些故事,会帮助你记住每一个字,”穆勒说道。汉语水平考试一共有六级,他已经过了四级,正在准备五级考试,这要求他认识2500个汉字。

照片库上海MBA学生
布莱特姐妹
瑞士姐妹在非洲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文:Anand Chandrasekhar,图:Georgina Goodwin
布莱特姐妹 非洲艺术
布莱特姐妹 非洲艺术


卢加诺人丹尼艾拉·布莱特说:“我没法继续在瑞士生活了,我觉得严密的控制令我窒息。”她现在52岁,生活在肯尼亚北部的拉姆岛(Lamu)。
她父亲来自提契诺州(Ticino)的艾罗洛(Airolo),她母亲是格劳宾登州(Graubunden)的蓬特雷西纳(Pontresina)人。在她19岁的时候,她离开了在瑞士意大利语区的家,来到了法国阳光明媚的圣特罗佩斯(St. Tropez)。她家里有三个姐妹、一个兄弟,尽管家庭关系亲密,但她心里还是产生了强烈的逃离祖国的冲动。
“瑞士确实很美,但我需要的不仅仅是美,”她说。“在这个国家生活对于年轻人来说太安逸了,我想要寻找一些挑战。”
但是迷人的圣特罗佩斯也没能令丹尼艾拉心满意足。那时她在法国蔚蓝海岸工作,在一个朋友的店里卖房子。七年过去了,她的心里又蠢蠢欲动起来。一次理发店之行最终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在浏览Paris Match Voyage旅游杂志的时候,她的目光定格在一张骑着非洲象的人的照片上。
她对瑞士资讯swissinfo.ch表示:“我一直梦想着在我的花园里养一头大象,而不是一条狗。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的梦想又一次被点燃了。我已经厌倦了圣特罗佩斯,我想要有点儿改变。”
她作了一些调查,发现这张照片拍摄于博茨瓦纳(Botswana)的一家大象康复中心。她随即给中心负责人写了封信。负责人一年后才给她回信,并邀请她到那里做有关大象的工作。由此,她又在这么个逍遥自在的地方开始了另一段奇妙的旅程。
“我们制作电影、广告,还组织大象旅游团,”她说。“这个项目致力于解救在世界各地的动物园里的状态不佳的大象,并把它们放回非洲的大自然。”
姐姐耳濡目染
几年以后,丹尼艾拉的姐姐玛丽亚娜也开始梦想离开瑞士。但是与她妹妹不一样的是,她的梦想并不是年轻人对新天地的渴求。那时她已经34岁了,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生活得非常安逸。
玛丽亚娜现在已经56岁了。她说:“有一天早晨,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不希望在余生继续这样的生活。我感觉太受束缚,瑞士对我来说实在太小了。”
玛丽亚娜想环游世界。她计划先在非洲落脚,探望丹尼艾拉,然后继续旅行。
丹尼艾拉表示:“我和姐姐实在太像了。我们志趣相投。”
一开始,两姐妹要离开欧洲奔赴非洲的决定令所有家人大吃一惊。但是家人们一直非常支持她们的决定。
丹尼艾拉说:“我的父母从不给我钱,但是他们告诉我,他们会一直爱我,家里也会一直为我留一个房间。这给了我离开的勇气。”
“如果我妈妈是我们这代人,她有可能会作出跟我们一样的选择。我爸爸是很传统的瑞士人,但是他理解我们要探索世界的渴求,”玛丽亚娜说。
丹尼艾拉和玛丽亚娜的兄弟姐妹们不像她们这么喜欢冒险。她们唯一的弟弟去了西班牙,而她们最小的妹妹则留在卢加诺,过着很惬意的生活。
丹尼艾拉说:“我妹妹的住处离我妈妈在卢加诺的房子只有200米远。她有丈夫,三个孩子和一条狗。并不是每个人都得离乡背井。”

照片库享受在肯尼亚的生活
尽管是大象把她带到了非洲,但是4个从3岁到18岁的孩子才让她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丹尼艾拉组建了一个公司, 用回收船帆制作背包,为当地渔民创造了宝贵的就业机会。(图:Georgina Goodwin)
非洲的现实
非洲的现实


当丹尼艾拉为大象奔忙时,玛丽亚娜得到了一份管理康复营的工作。这个机会让她无法拒绝。
她说:“我回到瑞士,卖掉了我的房子、车和所有东西,然后回到了博茨瓦纳。”
两姐妹每天忙碌于康复营的工作,但她们不会一直停留在博茨瓦纳。
有一次,玛丽亚娜去开罗检查两只大象的运输情况,她被途中触目可及的赤贫惊呆了。
“在看到路边的那些人后,我感觉我不能只为大象募集善款了,在这个大陆上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亟待解决,”她说。
几年后,当丹尼艾拉的一只心爱的大象遭到囚禁时,她的梦想也幻灭了。
她说:“我告诉他们,只有他们把我的大象放归野外,我才会回来。两年后,我回去看到它回到了大自然。我跟着他走了三个月,直到我确定它安好,我才回到肯尼亚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重新开始
丹尼艾拉在内罗毕遇到了一位英国海洋生物学家,并爱上了他。可惜他们缘分未到。她说:“他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我现在仍旧感觉很受伤。”
为了从感情创伤中走出来,她承担起一项拍摄肯尼亚拉姆岛上的渔民的任务。她对这个地方和当地的渔民们着了迷。
她说:“拉姆岛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这里没有车,没有迪厅,也没有赌场。它纯洁无暇,在这里我就好像永远在热恋中。”
但是对于当地的渔民们而言,生活却不那么称心如意。来自拖网渔船的竞争和雨季危险的海域使得他们生计艰难。其中一个渔民Ali Lamu找到丹尼艾拉,想找份工作。她思索着怎么才能帮上忙,最后想出了个颇具创意的点子。
丹尼艾拉说:“我受到了他们船帆上所用材料的启发。我在其中一个上面画了个大大的桃心,并加上了一句‘Love Again Whatever Forever’,然后又把它装裱起来。”
她求一个朋友把这个作品摆在店里。也就一小时后,这个作品卖出了180欧元 (193瑞士法郎)。在渔民们的帮助下,丹尼艾拉又做了几个作品。不久她就攒够了钱,开始做生意,将废旧的渔船帆改制成艺术品和包包。
她用渔民Ali Lamu的名字为该品牌命名为“Alilamu”。如今他们有30位全职雇员,其中Ali Lamu是现任董事长。丹尼艾拉说:“Ali Lamu是我的顶梁柱、朋友、兄弟和最有力的支持者。”
Lamu的生活也在他向丹尼艾拉求职的那一刻改变了。
他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现在我为我的家人盖了个小房子,并能够送我的孩子们上学了。当我还是渔民的时候,我只能租一个房间,还经常为支付房租而发愁。”

照片库在坦桑尼亚找到归宿
她创建了自己的公司,和200名马赛族妇女一起为世界各地的女性制作精美的首饰。她现在住在坦桑尼亚北部一个农场的帐篷里,一匹马和两只狗是她最亲密的伴侣,她就想这样一直生活下去。(图:Georgina Goodwin)
坦桑尼亚的艺术
坦桑尼亚的艺术


她爱上了一个非洲通保罗·奥利弗(Paul Oliver),并嫁给了他。保罗在坦桑尼亚北部的阿鲁沙(Arusha)附近组织观兽旅行。玛丽亚娜把旅行营地经营得很成功,但这份工作并非她的心之所向。过了一阵子,一个在米兰运营一家非政府组织的朋友给她带来了一个机会,令她心动不已。
“她有个项目,想通过推广马赛族(Masai)妇女的珠串首饰来提高她们的收入。她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这个项目。我接受了这份工作,条件是有朝一日该项目可以独立运营。”
两年后,这个项目已成为一家独立的公司,名叫“坦桑尼亚马赛族妇女艺术”(Tanzania Maasai Women Art)。共有200名马赛族妇女在这里工作。妇女们保留整体收入的10%用以维持发展,比如修缮她们的小棚屋。
玛丽亚娜说:“这里的99%的妇女都目不识丁且生活困苦。我无法让她们的艰难生活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至少这些珠串挣的钱可以使她们更加自信和自重。”
她们的生活确实艰苦。马赛族妇女不得不打柴、挑水、为一家人做饭,然后还得照看牲口。她们的意见通常为族群所忽视,同时她们还经常遭受虐待。
玛丽亚娜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赢得她们的信任。她希望有一天马赛族妇女可以自己经营这个生意,而她则可以离开并开始她下一个项目——一个为残疾儿童提供马术疗法的中心。
马赛族人玛格丽特·加布里埃尔(Margaret Gabrie)l说:“玛丽亚娜个性很强。她喜欢她做的事情,并且很会鼓励人。妇女们在接到新订单时都非常高兴。”玛格丽特于2016年四月离开公司,之前一直负责零售工作。
瑞士?规矩太多!
尽管这对姐妹每年都要回到家乡一次,但是她们已经同瑞士渐行渐远。
丹尼艾拉说:“当我在瑞士时,我觉得我像是在度假。一切都是这么的干净有序。”在她的假期里,她吃瑞士食品,行走在山里,到全国连锁超市Migros购物。
“我觉得我更像非洲斯瓦希里(Swahili)人,而不像瑞士人,”丹尼艾拉说。“我喜欢人们准时到达,但如果他们没有,我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丹尼艾拉已经融入拉姆当地社会。她收养了四个当地的孩子,年龄从3岁到18岁不等。当地人甚至还给她取一个本土名字,叫Khalila。
她说:“拉姆很美、很宁静,这对你的健康和心灵都很有益处。我起床后,走到海滩看日出和日落。与此同时,如果我想做生意,我也可以乘坐火车到繁华的地方去。”
尽管会想念瑞士巧克力,但丹尼艾拉表示她没法再居住在瑞士了,因为她觉得受到太多管制。她说:“这里有那么多的标志牌告诉你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拉姆,尽管身边有这样那样的危险,但我们很自由。”
一个一直存在的威胁是武装组织青年党(Al Shabab),该党已经在拉姆附近地区实施了几次袭击。索马里也离这里不远。
她的生意伙伴兼朋友Ali Lamu说:“在岛上没有青年团的袭击,但是在几个月前收到恐怖威胁后,安全部队在公路上,沙滩上和大宾馆里随处可见。”
拉姆一直为丹尼艾拉所承担的责任而担忧,比如说她收养的四个当地孩子。他说:“她慷慨仁慈。但有时她孤立无援时也需要别人帮助,比如当她收养的女儿生病时。”
棚屋生活和开放空间
她姐姐玛丽亚娜的生活也跟典型的瑞士生活相去甚远。她生活在一个朋友农场里的一个蒙古包风格的帐篷里。和她一起的还有一匹马,两条狗和一头驴。
她说:“瑞士是弹丸小国。我喜欢开放的空间:像是这里的山、森林和大草原。”
玛丽亚娜很难提前安排自己一天的日程,因为正如坦桑尼亚人的日常生活一样,她的工作时有意外发生。但当事情不那么混乱时,她挺喜欢同时做好几件事。
她说:“每天一早我要骑马,然后去位于阿鲁沙的商店和办公室。我晚上回家,带着狗一起散步,看夕阳西下,有时会和朋友们喝几杯或是共进晚餐。’
不像博茨瓦纳,这里没有危险的野生动物,比如狮子或猎豹。这里只有小的肉食动物像是鬣狗和豺。玛丽亚娜可以在附近自由走动。除了动物外,这个地区还是马赛族人的家。他们的棚屋或牲畜棚点缀着四周的村庄。在周末时,她会骑着车到马赛族村子里,和人们聊聊可以为他们创收的机会。
但是这并不全是明信片里的非洲。
她说:“许多人羡慕我生活在非洲,但是有时也很艰难。事情经常出问题,而这里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
她与丈夫两地相隔,凡事基本靠自己,只有几个朋友。但她觉得,目前她不会返回瑞士。她说:“瑞士就像个小岛,这点在人民的思维方式中体现的很好,它经常被条条框框束缚住。”
她确实想念雪和滑雪,还有瑞士的秩序感。
她表示:“在第三世界的条件下,我们很难为第一世界制造商品。坦桑尼亚人的不紧不慢有时真令人沮丧。”
前路飘渺?
她之前的同事玛格丽特·加布里埃尔(Margaret Gabriel)很为她担心。她说玛丽亚娜事必躬亲,为了这个公司呕心沥血,而加布里埃尔则对公司的未来感到担忧。
玛丽亚娜说:“她必须考虑到更新换代,因为有些妇女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没法再做珠串了。她需要同年轻女孩子们开展项目,为公司的将来作准备。”
尽管工作负荷大,且肩负200名马赛族妇女的重担,玛丽亚娜从未后悔。“我在实现自己的梦想。虽然我没有腰缠万贯,但我拥有一切我需要的。我心如止水,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
她的妹妹丹尼艾拉则有些建议给其他那些梦想着有一天逃离的瑞士同胞们。
“我的朋友们说我很勇敢,但我不太明白。其实在瑞士度过余生更需要勇气。跟着感觉走,不要害怕或者担心金钱,如果你敞开心扉,一切皆有可能。”

夏尔维亚·布鲁格尔
野性自由的顽强与第一次参加阿拉斯加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瑞士女人的信件往来文:Philipp Meier,图:Trent Grasse
夏尔维亚·布鲁格尔 阿拉斯加的冒险者
夏尔维亚·布鲁格尔 阿拉斯加的冒险者


这里是关于我的一个简短介绍,这是我第一次写这样的东西,我根本不知道,是否应该开这个头儿。
夏尔维亚·布鲁格尔(Silvia Brugger)就这样以类似书信的形式开始讲述她自己的移民故事。正如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一样,认识她是通过Facebook 。
下面的内容来自我们的合作伙伴,因此我们不能保证这些内容能够正常显示。
我以前在卢塞恩交通学校的一位老同学向我推荐了她。我在Facebook上给她留了言,幸运的是,夏尔维亚回复了我。我请她讲述她的经历,于是她理所当然地启用了现在普遍通用的“用户原创模式”(UGC):自己撰写她的经历。我唯一做的就是在文字的中间和结尾追加了一些问题。那就让我们开始读她的故事吧!
1974年我出生在楚格州的Cham,并在那里长大。我们一共兄妹5人,除了我的双胞胎弟弟马克斯之外,我还有3个比我们大4岁和8岁的姐姐和哥哥。我的两位姐姐也是双胞胎。
当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就经常在欧洲旅行。我的祖父母住在德国北部,我们 家族中有几匹“冰岛马”,我和我的姐姐们几乎每年都去国外参加骑马比赛。
完成基础教育之后,我去了卢塞恩的交通学校,因为我想毕业后能在瑞航Swissair工作,因为这能满足我的探险欲。我曾经在珀斯学了几个月的英文,之后便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周游澳大利亚,那一年我们才18岁。
毕业之后,我便开始规划我的职业生涯。在苏黎世Carlton Elite酒店完成商科学徒之后,我在圣莫里茨Badrutt’s Palace获得了一个季节性工作机会。
你在圣莫里茨的酒店里学到了什么?
我想想,印象有点模糊,可能因为我每晚都出去玩,而且喝了太多啤酒的缘故吧!:-)
我想说的是,我在美国非常留恋那些在瑞士学到的东西,在这里却用不上,比如自律和责任感。要想成功,这两点在职场上都非常有用。
举一个例子:美国的司法业务真是令我抓狂,一个人在麦当劳买了一杯咖啡,把舌头烫了,于是把麦当劳告上法庭,得到100万美金的补偿???我真搞不明白居然能有这样的事。但是随着时间,这些事都变得正常了,这里不需要什么“公共精神”。
1997年我去加拿大旅游的时候,认识了威利斯(Willis)一家,他们不仅养了冰岛骏马,还饲养雪橇狗。贝尔尼和詹奈特·威利斯临时邀请我去阿拉斯加玩几周,于是我人生第一次去了阿拉斯加。
在圣莫里茨的季节性工作结束之后,1999年我离开瑞士,移民阿拉斯加,同一年我与安迪结婚,他是贝尔尼和詹奈特的大儿子。
2001年我和安迪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们在一次拍卖中买下了这座小楼,用了一年的时间打扫、整理、翻修和装修。
我从未想过,我的童年梦想拥有一座垂钓和打猎小屋,有朝一日真能成真!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充满冒险:我们有了自己的渔猎小屋;我们整个夏天都在钓鱼;春秋天去狩猎;冬天的时候我们就训练狗拉雪橇。
安迪和他的家人热衷于参与世界知名的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家里的每位男成员都参加过不同年份的比赛。2007至2008年我们的狗拉雪橇队伍相当出色,这时候轮到我大显身手了:我率领我的狗队完成了1000英里的长跑比赛,我是第一位参加艾迪塔罗德比赛的瑞士女性。

照片库我在阿拉斯加的生活
我们分开后,我就独自在美国最北端的州最大城市安克雷奇生活工作。尽管如此,我让自己尽可能多地接触大自然。我很乐意在这里给你展示我的生活。(图:Trent Grasse)
狗拉雪橇比赛令你着迷的是什么?
狗拉雪橇比赛令你着迷的是什么?


我一直特别喜欢动物,但是在我们长大的公寓里,我们只能养两只猫。我们的第一条狗是在我16岁的时候当我们搬入一座房子以后才有的。
拉雪橇的狗当然不能与家犬相提并论,它们是用来工作的。多少代以来,它们被驯养成役畜,用来“工作”。
与狗出去遛个30、40英里当然是件很轻松自在的事。
我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而且喜欢挑战。因此我养这些狗不是为了好玩,我很快就开始参加短程比赛(200、300英里),我组了一支由20条狗组成的队伍,为艾迪塔罗德比赛作准备。我用了7年的时间训练它们,我亲手把它们养大,和我们的丈夫一起把它们训练成赛犬。
与这群狗在一起能带来各种不同的感受!非常冒险,有时候甚至很危险,稍不注意就会出事。在野外很容易迷路;野生驼鹿还有可能袭击狗群,令狗受伤或者死亡;还有就是严寒:零下30°C至40°C在这里并不罕见。从11月到1月这里的白天很短(10:00-15:00)。这就加大了训练的难度,因为训练要从早8点到晚6点。
进入隆冬之后(2、3月份)天又开始变长,如果没赶上特殊年份,这里的雪况非常理想,气温也舒服(零下10°C-20°C),这样的情况,当我与12只赛犬训练的时候,就已经很满意了。常常除了狗的喘息声之外,世界悄无声息,这种时候我会感到害怕。然而有的夜晚,如果在外面,可以看到美丽的极光。
当然参加比赛还需要经受自身的考验,尤其是参加像艾迪塔罗德这样的比赛更是如此!1000英里是非常遥远的距离,根据天气和路况,完成整个行程需要约9天的时间。能走完这一段路的人,背后不知凝聚着多少艰辛的汗水。
我用了10天的时间完成这段路程,具体的数据可以参阅www.iditarod.com网站(在Archiv一栏中查找2007年和2008年的Silvia Willis),2007年是我参赛的第一年。
参赛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刺激,因为作为首次参赛者,你根本不知道前面等待你的是什么。天气并不很差,但是那也是最冷的一年之一,许多参赛选手和狗都有冻僵的迹象。达到目的地之后,我的整个脸都肿了起来。比赛过程中,我的左手严重发炎,不得不去救护站,一位来帮忙的非专业护理有一个救护箱,他帮我进行了简单的处理。
时间长了,这样的生活对我们的婚姻产生了负荷。我和安迪不久之后就离婚了。我现在从”野外“搬到了城市,过起了”城市人“的生活。
狗拉雪橇比赛为我的生命带来无尽色彩,我很怀念那段经历。但是这些赛狗也很花费时间,我们从来没有度过假,因为天天都要喂狗,盛夏的时候是训练休息期,而这个时候又是我们的渔猎旅店的旺季。
现在我为K&L批发公司工作,是啤酒销售团队的负责人,手下有6名工作人员。
你在那里具体做些什么?
K&L是阿拉斯加的一个酒精饮料批发公司,我负责几个地区80家酒精饮料店的销售工作。
这些内容可能超过了你想知道的,希望你能通过这些对我的生活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你最思念瑞士的什么?
我思念很多东西。瑞士的公共交通与阿拉斯加相比简直太无敌了。阿拉斯加的面积太大了,所以从财政上考虑,修建一个覆盖面广的公交网络根本不可能。我也想念瑞士到处都是漫步路径,阿拉斯加虽然有许多自然景观和山脉,但是大多比较偏远而且也比较危险(许多野生动物出没)。作为瑞士人,我当然在巧克力的口味上也比较挑剔,所以每次我从瑞士回来,都要在行李里塞满巧克力。
我经常把阿拉斯加和瑞士作比较,并问自己,我剩下的生命时光应该在哪里度过?应该回到瑞士,离家人近点?哪里的经济状况和医疗保障更好?等我得到“正确”的答案,估计还需要很长时间。两个国家(美国和瑞士)都有它们的优缺点,所以很难取舍。
在美国比较容易实现自我,也比较自由。如果我说美国,我指的就是阿拉斯加,我不能想象在纽约、芝加哥或者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生活,阿拉斯加还能与瑞士相提并论,我主要喜欢这里的山。
在我的印象里,瑞士似乎非常正统,很多事情都被国家严格规定。瑞士相对较小而且人口密集,每次回瑞士,我都几乎患上幽闭恐惧症。
你与在瑞士的亲朋好友怎样联络?
我基本上都通过Facebook-我非常享受这个社交媒体-在Facebook上了解到以前的同学们都在做什么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如果没有Facebook这是不可能的事。通过„Hangout“我也经常与我的姐姐和爸爸联系,每两个星期我们在网上会一次面。
我现在已经在美国生活了17年了,虽然美国并不完美,但是这里比较容易实现梦想。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我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来形容。而如果在瑞士我的生活将一切按部就班:上学、学徒、找工作,用我的余生工作为退休攒钱。
而且我对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的担忧也比美国多。但是整个世界都在变化中,所有人都被卷进其中,无论在哪里生活。在阿拉斯加我们非常依赖自然资源,目前我们正在面对很大的国家赤字。这令许多人为未来担忧。
但我也很担心欧洲,所以我觉得瑞士不加入欧盟是对的,这样受到负面经济发展的影响就相对小一些。但是瑞士毕竟在欧洲,被欧洲国家所包围,多多少少也会受些影响。
我不是因为不喜欢瑞士而离开,我当时遇到了拓展自己的机会,并利用了它。我很骄傲我是瑞士人,热爱我的祖国也喜欢回瑞士旅游,但是每次假期结束,我也很高兴又能回到阿拉斯加的家。

侯思德特勒夫妇
克里斯蒂娜和汉斯·侯思德特勒从伯尔尼高原到巴拉圭原始丛林文:Marcela Aguila,图:Rodrigo Muñoz
侯思德特勒夫妇 巴拉圭的天堂
侯思德特勒夫妇 巴拉圭的天堂


“想不想回瑞士?一点也不!” 克里斯蒂娜不假思索地说道,“在这里,我们有自由和创造的可能,而在瑞士,我们连想象的能力都没有。”
拥有自由的他们在巴拉圭做了很多事儿:成立了一家自然保护协会,发起了一个生态旅游项目,开发了一家生态农场。为了向自己的家乡瑞士小村Gambach致敬,他们给自己的农场取名“新Gambach”。在那里,瑞士资讯swissinfo.ch记者分享到了农场自产的面包、盐和夫妇俩36年海外瑞士人的难忘经历。
从思乡、家庭、朋友谈到“有序、整洁”的瑞士文化。但说到底,巴拉圭才是他们的家,两人坚持道。在Alto Vera、Itapúa和圣拉斐尔国家公园(Parc National San Rafael)附近,汉斯亲手建造了自己的家园。
冒险的事业
克里斯蒂娜和汉斯的故事和大西洋沿岸巴拉圭最后的原始森林紧紧相系。这里是地球生态系统最丰富的地方之一,面临的环境威胁也最大。
说到危险,2008年的一个周日让克里斯蒂娜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正好有足球比赛,我一个人在房子里,听到外面有动静。我刚走出去,就迎面看到一个头戴黑色面罩、手握左轮手枪的人。”里斯蒂娜也没搞清,究竟是自己命大,还是射手的枪法太差,总之子弹并没有击中她。
汉斯也是一样:有一次,他驾着小飞机,在高空搜寻非法森林开发、火灾或非法种植的行迹时,不明人士曾向他的飞机射击。
“他们原来以为,只要把我们杀了,战斗就会结束。可是现在他们明白了,我们并非孤军奋战,”克里斯蒂娜用胜利的口吻说。
高原的寒冷
我们先回到冒险的起点:上世纪70年代末的瑞士的伯尔尼高原。克里斯蒂娜和汉斯在Rüschegg 镇的Gambach村过着波澜不惊的日子。也许是太平静了,所以,当听说可以在大西洋另一端购买土地时,夫妇俩都跃跃欲试。
在家人的经济支持下,他们买了250公顷的土地,来到这个新世界,他们却觉得一切都有些过时。“什么都像回到了50年前,”克里斯蒂娜打趣说。他们当年买下的天堂,荒凉到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瑞士尽管寒冷无趣,但那里的生活至少稳定安逸。
1979年2月,怀抱着大女儿布丽奇特,克里斯蒂娜来到巴拉圭。汉斯在6个月前已先行到达,为了清理土地:这位老船员砍树拔草,花了好一番功夫,才拾掇出为家人修建木屋的地方。
几年下来,心灵手巧的汉斯把木屋建设得越来越完善。他甚至架设了水坝供电,同时,小水库也形成自成一体的群落生境。另外,他还将邮寄来的超轻型飞机零件组装在一起,信心满满地要亲自动手制成飞行座驾。

照片库瑞士移民在瓜拉尼森林中的天堂
奋斗的岁月
奋斗的岁月


不过同时,农场初见成果。确切说是农场“收获”了第一批自产牛奶。克里斯蒂娜学会了制作奶酪(在巴拉圭,不是在瑞士),生态黄豆的种植也非常成功,克里斯蒂娜夫妇全心参与环保。一家人还添了丁:布丽奇特后来又有了一个妹妹特雷萨和一个弟弟佩德罗。
回到飞机的话题:它得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基金支持,这是森林生态保护组织Pro Cosara协会(德)获得的外部赞助之一。1997年,克里斯蒂娜夫妇发起创建的这家协会以保护近百年历史的自然保护区为使命,并力图追回未获政府承认的私人占据的土地。
由于私人占地,7.3万公顷的土地都无法回归生态园。同时,黄豆种植、非法作物种植以及森林的非法开发让这些土地深受过度开发的威胁。
新的领域
克里斯蒂娜和她的团队为了协会的壮大不懈地工作着。目前Pro Cosara已经拥有广泛的国际支持及联络网。协会已经实现了多个保护区统计研究项目,并致力于发展环保教育,培养人们的环境意识,推动可持续发展活动。
协会前途大好,克里斯蒂娜也在2016年2月离开了会长的岗位(她依然是董事会成员)。现在,她正在开辟一个新的“环保阵地”:生态旅游。就在不久前,几位美国大学生来到生态园,搜集到了当地70多种鸟类的资料。
生态园是真正的天堂。而在克里斯蒂娜夫妇眼里,他们的故乡伯尔尼高原也一样诗情画意。移民海外的决定到底是不是对的?“这是最正确的抉择,”克里斯蒂娜毫不犹豫地回答。除了自由,夫妇俩还十分庆幸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大自然中,怀着对自然的尊重而长大。
瑞士一直在心里
农产、家庭、耕作、环保:这些足够让人生充实。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忘记瑞士的故乡。
两个女儿现在都在瑞士生活,老夫妇也时常回去看看。在巴拉圭,他们经常参加瑞士移民组织的活动。为了在当地生活的瑞士退休老人能够继续得到养老金,克里斯蒂娜也义务工作了5年。
离开故土40年后,克里斯蒂娜怎样评价自己的祖国呢?“瑞士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它已经不是我们记忆中的瑞士了。我们的父母曾经常年和外国人共事,后者拥有自己的权利,也无心将他们的文化强加给瑞士。如今的情况看来很不一样,我担心瑞士会失去它的身份定义。”
对于想移民海外的瑞士人,她又有什么建议呢?“在最终决定之前,应该到目的地国生活至少3个月。有些人,人还没走,就先兴师动众把家什用集装箱都运出了国,等最后发现移民生活与自己的想象不一样时,已经为时已晚。”
虽然当年举家出国时一腔热情,克里斯蒂娜夫妇并没有把全部家当带走:他们的家具很长时间都存在了Rüschegg镇。其实,直到不久前他们才把全部家当都运到了巴拉圭。所以说,虽然移民生活很顺利,但他们从未打算破釜沉舟。

布鲁诺·曼瑟
布鲁诺·曼瑟回归简单生活文:Ruedi Suter,图:布鲁诺·曼瑟基金会
布鲁诺·曼瑟 马来西亚的烈士
布鲁诺·曼瑟 马来西亚的烈士


“马来西亚政府和木材集团试图让布鲁诺·曼瑟(Bruno Manser)闭嘴,”2003年末,巴塞尔民事法庭这样就曼瑟的失踪案宣布。曼瑟,在巴塞尔长大,虽然热爱生命,但决不愿以无知、毁灭和剥削为代价,也不愿再付出他曾浸身其中的工业社会的代价。他深知,工业社会是以预支、以抢夺原住民和自然为代价发展的。面对这个过剩的社会,他选择了苦修:他奉行极简的生活。因此他拒绝了现代生活,尽管凭他的智慧、创造力、执着和幽默这些都唾手可得。
曼瑟拒绝上学,却成为高山牧场的牧羊人,他在山上过了11年。“我想知道一切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知识”。他在寻找靠捕猎、采集为生的人群,就像原始社会那样,在那里他可以把所学付诸实践。在科技发达的欧洲,他找不到这样的人类。因此1984年他到访马来西亚砂拉越(Sarawak)的婆罗。在那里他穿越原始森林真的找到了仅有300多户的本南人,他们完全以游牧的形式生活在雨林中。
他们竟然接受了他!他扔掉了他所带来的一切:衣物、应急药品、牙膏、鞋子。近视的他只把眼镜留在了鼻子上。他强迫自己光脚走路,一开始很痛,还要定期用刀子把荆棘挑出来。他学会了忍受痛楚,因为本南人就是这样在丛林中生活的,必须接受疼痛。于是光脚渐渐成为习惯。这象征着一种解放,他,一个现代人,不再依赖鞋子了,这是他的成功!
他们中的一员
他很快赢得了尊敬,完全融合在本南人的生活中。光脚走路、裸体、忍饥挨饿、潮湿、昆虫、欧洲医蛭,甚至还有皮肤溃疡和痢疾,都成为日常小事。最后,这位戴眼镜的人真正如本南人一样生活在丛林中,和他们披荆斩棘、蹲下休息、游过泛滥的河流、在树冠高处搭建夜间休憩处。
他喜欢这种丛林游牧人的简单生活,就好像又拾起了他家上辈子的生活。他不希望再回到瑞士,回到那逼仄、尾气、噪音丛生的世界。那些人总是在绞杀其他物种,距离自然生活越来越远,用科技、金钱和娱乐工业追逐人生意义,却往往又迷失其中,或让自己变得更加沮丧。不,他要和那些简单、热心的人生活在一起,感受他们的幸福和不幸,为了他们共同栖身的原始森林而欢唱。尽管他还是有隐隐的思乡之情,不是对瑞士,而是对他的家人、朋友。灵魂的痛苦总是让他拿起笔写信,或是寄回录音带,但这并未让他放弃他的雨林家庭。是的,他到了,到了他的伊甸园,那里的一切正如他所想,他为什么要离开那里呢!
他由此成为“本南之子”(Laki Penan),他学会在野外生存,抛网捕鱼、用吹箭筒和毒箭捕猎,用矛和火枪捕熊、猴子、野猪、鹿和鸟,采集森林水果和硕莪。他学习他们的语言、记下他的观察,留下难以数计的对人、动物和植物的记述。可能那时他就预感到,这里庞大的森林世界、清澈的水流、丰富的野生动植物,有一日终将被摧毁。
因为林业集团已经摧毁了森林中的许多地方,在政府的准许之下,他们无视地权和靠森林水果为生的丛林居民与日俱增的贫困。对砂拉越首府古晋的政治家来说,雨林就像自助商店:参天大树的硬质木材被出售,只为了满足工业国家消费者对阳台、家具和高级游艇和窗框的需要。

照片库热带雨林中的一分子
20世纪90年代,他一夜成名,因为他用绝食60天的方式在国会门前示威,要求关注原始森林中受到威胁的本南土著。
2000年布鲁诺·曼瑟消失在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中,5年之后这位积极的环境保护者被官方宣布死亡。但是他的精神得到延续:环保组织在巴塞尔成立了一个布鲁诺·曼瑟基金。(图:布鲁诺·曼瑟基金)
国家头号敌人
国家头号敌人


可是电影摄制组来了,他们将他作为勇敢的雨林保护者,拉到镁光灯下。对于世界媒体来说,他成为了“白色野人”-本南的代言人,他的出现总是那么低调,声调平和,言辞恳切,可突然之间,世界都在倾听他,曼瑟成为了反抗的代表,成为了反对乱砍乱伐雨林的英雄。
“为了向全球市场提供廉价木材,本南人的生活空间却受到了摧残,1990 年我回到瑞士,为了在我们的文明中发出本南人的声音-‘不要用我们的森林建你们的房子’”,在巴塞尔人权斗士Roger Graf 的帮助下,他成立了保护雨林的‘Bruno-Manser 基金会’,主要目标是:呼吁所有工业国家的消费者拒绝热带木材。
这个基金会强调,狩猎、采集人群与他们的生存空间共生:“森林死,人类亡”。他向欧盟,联合国,热带雨林木材组织ITTO不厌其烦地讲述本南人令人绝望的处境。在瑞士,他生活及其简朴,到访许多地方。他还在反对婆罗对本南人的暴行,他越来越激进,因为留给本南人的时间不多了。
失踪
曼瑟在瑞士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绝食抗议,要求木材供应和生产商履行申报义务,但没有结果。“饱汉不知饿汉饥”,砂拉越(Sarawak)的森林还在消失,动物们都被驱逐了。健康的本南人变得困顿交加, 1996年70%的原始森林遭到毁坏,这位雨林守护者还在欧洲和砂拉越(Sarawak)用行动表达着他的关切,并希望引人注意,但这一切都毫无用处。 2000年布鲁诺·曼瑟回到婆罗,并就此失踪。
他被杀了么?被毁尸灭迹?失踪几乎等同死讯,因为到目前为止,鲜有证据显示他发生事故或者自杀。他的失踪成为一个谜团,他的亲友不再等待布鲁诺,他们知道他就在那里,他的心,他的思想。恍惚中他们能听到他富有力量的声音:“只有行动才算数,包括你的行动!”
Ruedi Suter,《Bruno Manser-森林之声》的作者

相关题目
瑞士人镜头里本南最后的游猎民族
在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的雨林里,生活着一支名为本南(Penan)的土著民族,瑞士摄影师Tomas Wüthrich展现了他们神秘的生活。从用吹箭筒捕猎到伐木毁林的步步紧逼,这都是生存环境面临严重威胁的本南人的日常。“可我并不是新一代的布鲁诺曼瑟,”他强调说
瑞士移民目的地:男女老少“各有所爱”
2018年,在海外居住的瑞士公民共计760'200人,比前一年又增长1.1%。而法国、德国、美国和意大利依然是瑞士人主要的移民目的地国。
最高龄的海外瑞士游子驾鹤西归,享年110岁
最长寿的瑞士游子老翁-出生于1908年的Rodolphe Buxcel于上个月在美国密歇根州寿终正寝,以110岁高龄与世长辞。上个世纪之初他生于沙皇俄国统治疆域内的一隅瑞士人聚居区,历经颠沛流离,最终在美国安家落户,在粗衣淡饭中安度晚年。
瑞士十字与雨伞之间
瑞士侨民(居住在国外的瑞士人)组织(ASO)在首都伯尔尼联邦广场举行其成立100年庆典。虽然大雨让人们撑起了雨伞,却丝毫没有影响他们节日的心情。没有带伞的人则可在帐篷摊位或屋檐下暂时避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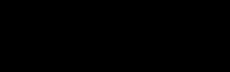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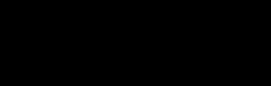 逃离金丝笼
逃离金丝笼
 在一个迎头赶上的国家里取得领先
在一个迎头赶上的国家里取得领先
 尼古拉斯·穆勒
尼古拉斯·穆勒
 上海MBA学生
上海MBA学生
 金色的安全网
金色的安全网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布莱特姐妹
布莱特姐妹
 享受在肯尼亚的生活
享受在肯尼亚的生活
 非洲的现实
非洲的现实
 在坦桑尼亚找到归宿
在坦桑尼亚找到归宿
 坦桑尼亚的艺术
坦桑尼亚的艺术
 与第一次参加阿拉斯加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瑞士女人的信件往来
与第一次参加阿拉斯加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瑞士女人的信件往来
 夏尔维亚·布鲁格尔
夏尔维亚·布鲁格尔
 我在阿拉斯加的生活
我在阿拉斯加的生活
 狗拉雪橇比赛令你着迷的是什么?
狗拉雪橇比赛令你着迷的是什么?
 从伯尔尼高原到巴拉圭原始丛林
从伯尔尼高原到巴拉圭原始丛林
 侯思德特勒夫妇
侯思德特勒夫妇
 瑞士移民在瓜拉尼森林中的天堂
瑞士移民在瓜拉尼森林中的天堂
 奋斗的岁月
奋斗的岁月
 回归简单生活
回归简单生活
 布鲁诺·曼瑟
布鲁诺·曼瑟
 热带雨林中的一分子
热带雨林中的一分子
 国家头号敌人
国家头号敌人
 交谈
交谈
 解渴
解渴
 思考
思考
 集市上的纪念品?
集市上的纪念品?
 保持联系
保持联系
 在马林迪,丹尼艾拉回家的路。
在马林迪,丹尼艾拉回家的路。
 丹尼艾拉虽然逃离了瑞士,却未能逃离坐办公室。
丹尼艾拉虽然逃离了瑞士,却未能逃离坐办公室。
 与四个孩子和手下的员工吃饭。
与四个孩子和手下的员工吃饭。
 去接孩子的路上。
去接孩子的路上。
 在马林迪的家也用来做车间。
在马林迪的家也用来做车间。
 放学之后,丹尼艾拉和孩子一起度过宝贵的时光。
放学之后,丹尼艾拉和孩子一起度过宝贵的时光。
 把回收的旧船帆变成时髦的背包。
把回收的旧船帆变成时髦的背包。
 丹尼艾拉喜欢新型图案,所以心型图案几乎是她系列产品的招牌。
丹尼艾拉喜欢新型图案,所以心型图案几乎是她系列产品的招牌。
 在拉穆阿里工作室中总是有干不完的工作。
在拉穆阿里工作室中总是有干不完的工作。
 在Shueb做饭的时候,丹尼艾拉休息一下。
在Shueb做饭的时候,丹尼艾拉休息一下。
 丹尼艾拉非常享受收养的孩子给他带来的“当妈妈”的感觉,放学之后是真正的家庭生活开始的时间。
丹尼艾拉非常享受收养的孩子给他带来的“当妈妈”的感觉,放学之后是真正的家庭生活开始的时间。
 当丹尼艾拉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会忘记工作。
当丹尼艾拉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会忘记工作。
 每周一上午整个销售团队在办公室里开会,我们共同计划本周的工作。
每周一上午整个销售团队在办公室里开会,我们共同计划本周的工作。
 与一位在安克雷奇拥有三家饮料店的老顾客Bryan Swanson谈话
与一位在安克雷奇拥有三家饮料店的老顾客Bryan Swanson谈话
 2015年K&L批发了大约270万箱啤酒
2015年K&L批发了大约270万箱啤酒
 我们的供货商同样友好地维持着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供货商同样友好地维持着我们之间的关系
 加利福尼亚Lagunitas啤酒厂代表拜访我们
加利福尼亚Lagunitas啤酒厂代表拜访我们
 我尽可能多地接近大自然
我尽可能多地接近大自然
 比如在“鸟溪”(Bird Creek)钓鱼
比如在“鸟溪”(Bird Creek)钓鱼
 “鸟溪”(Bird Creek)离安克雷奇只有20分钟车程,因银鲑鱼而闻名。
“鸟溪”(Bird Creek)离安克雷奇只有20分钟车程,因银鲑鱼而闻名。
 这头黑熊是大约我十年前在Beluga射杀的。这三条金毛猎犬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头黑熊是大约我十年前在Beluga射杀的。这三条金毛猎犬是我最好的朋友。
 只有完成过艾迪塔罗德(Iditarod)狗拉雪橇比赛的选手(所谓的“Musher”)才能在阿拉斯加拥有这样特殊的车牌。22号是我曾取得的最好成绩(2008年)。
只有完成过艾迪塔罗德(Iditarod)狗拉雪橇比赛的选手(所谓的“Musher”)才能在阿拉斯加拥有这样特殊的车牌。22号是我曾取得的最好成绩(2008年)。
 我喜欢和我的狗一起散步
我喜欢和我的狗一起散步
 我的两条浅色狗,一条叫Myla (16岁) ,一条叫Oscar (Myla的儿子),它们的寿命可能不会很长了,所以我去年决定又买了一条- Alina,它们俩很大方地接受了它。
我的两条浅色狗,一条叫Myla (16岁) ,一条叫Oscar (Myla的儿子),它们的寿命可能不会很长了,所以我去年决定又买了一条- Alina,它们俩很大方地接受了它。
 远离人群,但并未与世隔绝:汉斯和他的一位朋友及朋友的狗Albi在他的房子前。
远离人群,但并未与世隔绝:汉斯和他的一位朋友及朋友的狗Albi在他的房子前。
 克里斯蒂娜在她的书房里。
克里斯蒂娜在她的书房里。
 克里斯蒂娜和汉斯·侯思德特勒为游客组织各种生态旅游活动。
克里斯蒂娜和汉斯·侯思德特勒为游客组织各种生态旅游活动。
 克里斯蒂娜·侯思德特勒在巴拉圭学会了制作奶酪。
克里斯蒂娜·侯思德特勒在巴拉圭学会了制作奶酪。
 35年多以来,汉斯·侯思德特勒一直很享受瓜拉尼森林茂盛的植被。
35年多以来,汉斯·侯思德特勒一直很享受瓜拉尼森林茂盛的植被。
 养鸡也是侯思德特勒家日常生活中的事务。
养鸡也是侯思德特勒家日常生活中的事务。
 汉斯·侯思德特勒利用自己的小型飞机巡查自然保护区,及时发现不法活动。
汉斯·侯思德特勒利用自己的小型飞机巡查自然保护区,及时发现不法活动。
 家庭菜园。
家庭菜园。
 几乎是天才手工工匠的汉斯在巴拉圭自己翻修了房子,并安装了所有所需的水电。
几乎是天才手工工匠的汉斯在巴拉圭自己翻修了房子,并安装了所有所需的水电。
 克里斯蒂娜和汉斯·侯思德特勒树林里散步。
克里斯蒂娜和汉斯·侯思德特勒树林里散步。
 休息的时候,传统的马黛茶是不可少的。
休息的时候,传统的马黛茶是不可少的。
 新Gambach的有机生态农场、侯思德特勒家的房子、田野和温室。
新Gambach的有机生态农场、侯思德特勒家的房子、田野和温室。
 1984年布鲁诺·曼瑟首次去了婆罗(Borneo)。
1984年布鲁诺·曼瑟首次去了婆罗(Borneo)。
 他寻找在原始森林中生活的本南土著人。
他寻找在原始森林中生活的本南土著人。
 1986年Alberto Venzago为布鲁诺·曼瑟拍的照片。
1986年Alberto Venzago为布鲁诺·曼瑟拍的照片。
 同样是1986年Venzago为GEO的一篇报道拍摄的照片。
同样是1986年Venzago为GEO的一篇报道拍摄的照片。
 人类对原始森林的破坏是巨大的。
人类对原始森林的破坏是巨大的。
 1993年3月:瑞士联邦委员露特・德莱富斯(Ruth Dreifuss)和布鲁诺·曼瑟在为联邦委员们织毛衣。
1993年3月:瑞士联邦委员露特・德莱富斯(Ruth Dreifuss)和布鲁诺·曼瑟在为联邦委员们织毛衣。
 1993年布鲁诺·曼瑟和Martin Vosseler在伯尔尼进行绝食示威,要求禁止进口热带木材。
1993年布鲁诺·曼瑟和Martin Vosseler在伯尔尼进行绝食示威,要求禁止进口热带木材。
 布鲁诺·曼瑟经常回到欧洲,为保护马来西亚和婆罗的土著人权益而奔走。(Keystone)
布鲁诺·曼瑟经常回到欧洲,为保护马来西亚和婆罗的土著人权益而奔走。(Keystone)
 本南人也出来为自己争取利益,他们聚集在砂拉越地区的巴拉姆附近示威。
本南人也出来为自己争取利益,他们聚集在砂拉越地区的巴拉姆附近示威。
 布鲁诺·曼瑟象本南人一样捕鱼和狩猎。
布鲁诺·曼瑟象本南人一样捕鱼和狩猎。
 一个本南女人,在喂一只犀鸟。
一个本南女人,在喂一只犀鸟。
 Ara Potong,一位已故的原是森林中Ba Pengaran Kelian土著人首领。
Ara Potong,一位已故的原是森林中Ba Pengaran Kelian土著人首领。
 布鲁诺·曼瑟和本南土著首领Along Sega。
布鲁诺·曼瑟和本南土著首领Along Sega。
 来自林梦地区(Limbang)的Peng Meggut现在还过着游牧生活。
来自林梦地区(Limbang)的Peng Meggut现在还过着游牧生活。
 2000年5月布鲁诺·曼瑟失踪之前在砂拉越的照片。
2000年5月布鲁诺·曼瑟失踪之前在砂拉越的照片。
 热带雨林的黄昏。
热带雨林的黄昏。
 赢得莫拉尼-马赛战士的信任,是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环节。
赢得莫拉尼-马赛战士的信任,是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环节。
 在一个车间讨论包包的款式。
在一个车间讨论包包的款式。
 制作繁复的首饰需要灵活的头脑和灵巧的双手。
制作繁复的首饰需要灵活的头脑和灵巧的双手。
 Gabriel是企业中少有的男性专家。
Gabriel是企业中少有的男性专家。
 在博马--马赛的公共活动中心,玛丽亚娜与她的团队见面。
在博马--马赛的公共活动中心,玛丽亚娜与她的团队见面。
 完成国际订单,需要详尽的生产计划。
完成国际订单,需要详尽的生产计划。
 年轻一代是想留在企业中工作还是前往大城市生活,还有待观察。
年轻一代是想留在企业中工作还是前往大城市生活,还有待观察。
 要去见一位马赛女工,需要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开50公里。
要去见一位马赛女工,需要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开50公里。
 玛丽亚娜在马鲁沙的店面培训新员工。
玛丽亚娜在马鲁沙的店面培训新员工。
 为了避免事故,检验车胎是非常重要的事。
为了避免事故,检验车胎是非常重要的事。
 在农场,总要记着关上闸门。
在农场,总要记着关上闸门。
 Piccola和Buffo是自诩的门卫。
Piccola和Buffo是自诩的门卫。
 随时都有可能接到与工作相关的电话。
随时都有可能接到与工作相关的电话。
 这样的厕所在丛林中是奢侈品。
这样的厕所在丛林中是奢侈品。
 玛丽亚娜的门廊是最美的地方。
玛丽亚娜的门廊是最美的地方。
 玛丽亚娜利用少有的空闲时间读些书。
玛丽亚娜利用少有的空闲时间读些书。
 车间里总是有人会来打个招呼。
车间里总是有人会来打个招呼。
 每天早上玛丽亚娜都要看看她的马Pink Fizz是否正常。
每天早上玛丽亚娜都要看看她的马Pink Fizz是否正常。
 每天晚上与两只爱犬散步是玛丽亚娜最喜欢做的事。
每天晚上与两只爱犬散步是玛丽亚娜最喜欢做的事。